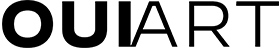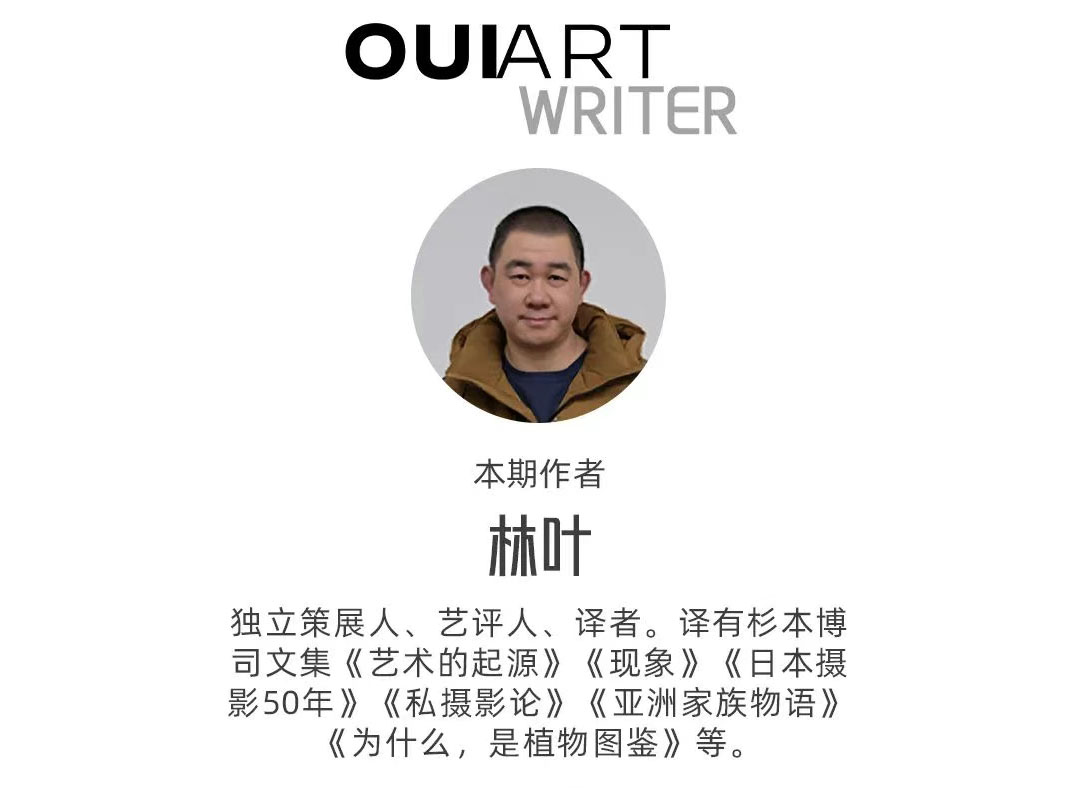此刻有谁在世上的某处哭,
无缘无故地在世上哭,
哭我。
此刻有谁在夜里的某处笑,
无缘无故地在夜里笑,
笑我。
此刻有谁在世上的某处走,
无缘无故地在世上走,
走向我。
此刻有谁在世上的某处死,
无缘无故地在世上死,
望着我。
——《沉重时刻》(冯至译)
一百多年前,里尔克以一首《沉重时刻》悄然击中了现代人心灵之中最隐幽深沉的弱点。所谓沉重时刻,就是我们意识到这个如影随形般附着在自己身上的“无缘无故”的时刻。当这一刻突然降临在自己身上,当身为个体的“我”清晰地意识到自己是人群中的一个“人”,这时候便仿佛有一道强光瞬间照亮了自己的意识,“我”从“我们”中脱落出来。我们才幡然醒悟,原来自己在这个世界上、在人群之中是如此的轻薄、如此的无助,原本猛烈跳动的心就一下子沉入深渊。
这大概也是爱伦·坡小说《人群中的人》里那位孤单地在街头游走的老人的生命处境,也是我们进入长沙谢子龙影像艺术馆蒋志个展 “人群中的人” 之后首先要面对的一种处境。展览的第一件作品《照耀我》中,每一个人在那道强光的照耀下,都显得不知所措,无所适从。这一刻,我们也都被拉进了他们的那种处境,身上沉积着的那种不知所措、无所适从被瞬间唤醒。
每一个人都是人群中的人,都是从人群中独立出来的个体。只不过在很多时候,我们总是习惯于以一种心满意足、有条有理的神态在人群中游走,我们的“所思所想的就只是穿过那蜂拥的人群”,就像在影像装置《人的几分钟》中穿行时所获得的那种体验——这些混杂、模糊、似乎含义不明的街头人群的影像被投影在展厅地面,展厅也因此转化成了某种拟真的街区,我们就像蒋志那样,在观察和拍摄人群中的对象的同时进行流动的、随机的、若即若离的、不经意的观看。不知不觉间,我们也融入到了街区之中,成为了其中一员。人群是晦暗而庞大的存在,人穿行其中却不知所踪。
因此,从人群中脱落也好,独立也罢,往往不是作为个体的我们主动选择的结果,而是因为生活中遇到的一些意外情况,让人猝不及防地遭遇到那个隐秘的“自我”,也遭遇到自我身上的那种复杂、孤单和脆弱。而这样的个体内在体验与人群无关,与其他人无关,与周遭世界无关。这时候,我们转身再次进入右边的展厅,面对设置在《照耀我》背面的作品《0.7%的盐》,默默地与那个巨大屏幕中的钟欣桐对视8分43秒,默默地看着她由微笑慢慢地转变为哭泣。
作为一名从人群中独立出来的个体,这一生,不论是微笑还是哭泣,这中间的一切都只能由自己一个人去承受。而平日里我们确信对构建自我、确立自己的社会地位、让自己拥有足够信心有所帮助的种种标签,如“知识”“自由”“贵贱”“天堂”“伟大”等,同样跟自己“无缘无故”,全都失去效用,就如《天空之吻》中所表现的那样,转瞬之间便被冲进马桶之中,消失得无影无踪。
从某种意义上理解,每一个个体只能通过切实的生命实践去生产个体与群体、自我与他者之间真诚的连接,让相互之间的“缘故”得以发生,那些带着荣光的标签才不会只是让人产生幻觉的致幻剂,而是真正落实在自己的生命与生活之中,成为有效的经验与智慧。如果说这三件作品让人深切地体验到人从人群中独立出来的那种孤绝状态的话,那么下一个展厅中的五件作品则从不同的角度向我们展示了孤绝状态下的个体对“我”的探索。
在《谢幕》中,我们看到一位女演员表演了一幕不愿意离开关注和掌声从而反复回到舞台的独角戏,她以一种不断谢幕的方式希望留在舞台上。这样的行为看似怪诞离奇,但却传达某种潜在在所有人内心深处的隐秘心理——我们总是不由自主地用各种方式展示自己的存在,表现自己的功绩,强调自己的重要性,希望能够受人关注,被人长久的记住,甚至能够将自己的行动痕迹深深地镌刻进历史之中。我们总是需要借助他人的目光、他人的评价来获得存在感,确定自己的位置。而《我们都是你的礼物》则以另外一种荒诞让人体会到当下社会中“我”的异化与破碎。可以说,这样的行为虽然荒诞离奇,但却是现实社会中大多数人探索“我”的普遍手段。这样的荒诞恰恰源自于人内心中那深重的孤独感。
世事无常,个体的灵魂在现实世界中难免孤单无依,如何让自己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行动来承担生命中的痛苦与责任,则需要我们在不断重复、周而复始的日常生活中去调整、适应和创造。在作品《空笼》中,蒋志拍摄了一个在深圳街头偶遇的小女孩。
小姑娘随身携带着一个空的鸟笼,走到哪里,她都牢牢地抓着这个带有某种家的意味的东西。一旦这个女孩被蒋志的DV捕捉下来,她的形象与行为也就成为了一种隐喻,成为现代人共有的孤独状态的隐喻。“拍摄过程中对‘空’的感受十分强烈——女孩周围如风般来来去去、聚聚散散的路人,看似凝固却飞逝的时间。关于同情和冷漠......关于缓慢和急速......关于执着与随机......一切又仿佛可被一笔‘空空’带过。”蒋志如是说道。可生活中,谁又何尝不是如此。我们竭尽全力地探索“我”的实在,不就是为了让这空空的鸟笼能够留住些什么吗?不论是将自己异化成某种坚固而冷漠的如玩偶一般的存在,在街头游荡闲逛,还是一个人在家中借助手掌的舞动来想象自由的质感,让生命获得些许诗意与光韵,我们所做的无非就是真正地理解“我”,认知“我”,通过真诚的生命实践将那个空虚而孤独的“我”填满,让“我”成为实在。
现实世界是由各种各样的困境堆叠累积而成,无数的困境,灌注在每一个脆弱个体的人生之中,如狂风一般,回旋飞舞,弧线交错纵横,却又形态一致,逼迫我们必须用生命孤勇地去承受转化,生成属于自己的“我”。在这样的世界中,每一个人都是一个混沌的宇宙,都是竭力成为独特之“我”的疯狂艺术的象征。在展览最终部分的那个小空间里,我们遭遇的就是这样的疯狂艺术。
这里展示的是四屏黑白影像作品《在风中》。蒋志“以沉浸式的影像呈现了个体面临猛烈外力时的竭力挣扎,也是人类在风雨飘摇之中险情的暗喻。”第一个屏幕中,一个人“在猛烈的风中肩负着轻重难辦的巨石”,如西西弗斯一般奋力向前,周而复始,不得解脱。第二个屏幕呈现了一个年老的背影在狂风中和童年玩具一同被风裹挟,却依然安步向前。第三个屏幕中,一个人在狂风中死死抱住一棵与他一样飘摇的树,努力支撑,始终不肯放弃。第四个屏幕呈现的则是一对情侣在狂风中互相搀扶着,虽难以前行一步却毫不退缩。
这个作品中最让我震撼的从来都不是那猛烈得要将人摧毁的狂风,而是每一个在风中用生命、用平凡的肉身对抗出“我”的深度与厚度的个体。
“我”不是一个平滑顺畅的直线,也不是坚固不变的物,更不是任意由各种现实碎片拼凑而成的拼贴物,或者被命运随意揉捏的橡皮泥,而是能够将盲目的命运砸在自己身上的一切主动承接下来、并用自己的行动积极地转化成生命养分的存在。当一个人积极果敢地去接受命运的无常并开创属于自己的独特生命的时候,我就是在“成为我”,在将自己锻造成一个具有“深度”和“厚度”的生命体,让自己拥有一种不因命运的无常而影响的精神主体的能力。这就是我从《在风中》这个作品中深切体认到的精神。
从展厅离开,再次进入“人群”之中,“我”不再是那个抽象的“人”,所有的作品聚合在一起,共同将“人”引向具体的、有深度与厚度的“我”。我们无需再将群体性的他者作为强大的参照系,也无须用各种手段将自己塞进他者的世界。相反,我们可以独立地在人群中,多视角、多层面地琢磨理解那狂风般的命运,并维系自己的精神独立性,从而获得能够凝聚自我的生命能量,于是,“人”就成为了“我”。
出品人:Tiffany Liu
编辑:Tiffany Liu
设计:Yizhou Shen
图片提供:来自谢子龙影像艺术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