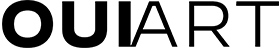Q1
OUIART:
没顶把美术馆空间,包括一些展览和项目活动设立在崇明对于整个没顶公司来说,这是一种补充吗?它是否代表了你们在探索方向上的一些变化?
徐震:
我觉得其实有一点像补充。最近很多艺术家来这里布展,因为没有安装灯,晚上天一黑就没有办法工作,我们大家就聊聊天。我自己的感觉是——首先,这里已然不是农村,而更像一种城市扩大其边缘的过程:其次,我们来这里不是来做乡建的,包括以前在上海广场这样的商场里做展,其实都是通过去这些地方来给自己找一些感受。艺术家或策展人需要去寻找一些新的语境和境遇来让自己进入到这种感受中所以,到崇明来是让它来改造我们,而不是由我们来改造乡村,这个跟所谓的乡建有着很大的区别。
另外,也有一些朋友会问到,你们有没有问过当地居民的感受。我后来发觉,在观看我们的作品时,当地居民与上海广场的那些观众们其实有着一样的好奇心。现实中,他们也是拿着小米或后辈留下的IPHONE,看着不知道是哪里的新闻。在这样一个城郊结合部,或者说城市的边缘,它本身的当代性问题依然存在。今天不存在逃离或者避世,只能说我们在这里找到某种别样的感受,然后拿出来跟大家分享,一起去做一些有趣的事情。

Q2
OUIART:
我们是否可以这样理解,对于一名艺术家或是展览策展人而言,崇明的没顶美术馆不论是从其所处的地理环境来看,还是从其本身介于当代现实和自然交界处的这样一个空间场域来看,它都提供了一个相对而言有着更多褶皱和肌理的空间,去刺激创作者展开更多的想象?
徐震:
是的,这个总结得非常正确。关于这里的改造,你们最后看到的其实是我们选择基本不改造,这就是你说的褶皱。甚至这里的绿化,也展现出了一种废墟感。我们之前有设想过找一些园艺师或建筑师来进行改造,但后来再一想,觉得把这里弄成那种中产阶级式的、漂亮舒适的地方感觉不太对。作为艺术家,我可能只是凭直觉就觉得不太对,所以还是保留了这里的废墟感。即使有塌陷的墙壁,我认为也是它天然的一种褶皱。美术馆的定位其实就是它要释放的能量和价值观;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画廊的妥协度要比这里高,而我们已经有画廊了,那这里还不如让它更野生。

Q3
OUIART:
从运营的角度来说,一个问题是,关于展览和作品的选择没顶美术馆会不会有一个基本的调性,还是说是开放式的?另外一个问题是,在选择合作伙伴上,未来有哪些考量?
徐震:
首先,我们是很开放性的。我们画廊在艺术家的选择上也很开放,没有太偏向某种风格类型。另外,我跟金利萍一起合作20多年了,从非营利性的比翼艺术中心开始,基本上做事情都是以艺术为最终导向,然后能保证机构正常的流通运转就行。凭我接触下来,大多数艺术家其实还是喜欢有一定挑战、未知性很强的事情,喜欢自己去决定某件事的意义,而不是去靠机构策划人和画廊老板来决定。
我的工作大部分是团队的集体工作。这次展览上,你看到的艺术家有些是学生,有些是刚出道的年轻艺术家,有些是在这驻留的,有些是我们画廊代理的,有些是其他画廊代理…但是大家关系都比较好,于是就变成了这样一个群体模式。我本身就是在这样的集体中长大的,目的性没那么明确地长成这样。有时候,我会觉得现在的人目的性太明确了,不像我们早期做艺术时那么轻松。太多焦虑下,人有时需要有个出口,崇明岛就有点类似这样一个出口。今天,一方面大家彼此间充满了各种隔阂和误解,另一方面大家好像又都是极度焦虑的。我们这样一种选择,其实蛮有时代特点,它不是我们主动的选择,而是像探路那样,最后大家共同找到了这样一种方式和结果。也许做几年又会发生什么新的变化,但其实都是在比较自然而然的一个系统下发生的。

Q4
OUIART:
所以当大家强调美术馆的自然生态时,这个生态也并不只是指外部的自然生态?
徐震:
对,它还包括行业、体制......整个艺术生态。大家在讨论生态时,其实这个生态更多指的是政治体制的结果,相关的管理方式、民族以及文化最终决定这里的生态是怎样的。所以现在说的生态是非常整体性的概念,大到意识形态,小到艺术体制的影响。

编辑:Simone Chen
撰文:李素超
图片提供:没顶美术馆
部分摄影:罗浩、Simone Chen
设计:Milkshake